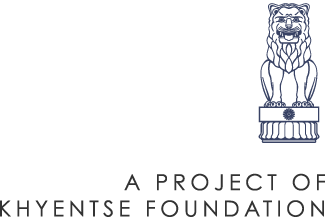2020年即将开展的佛典汉译工作
2019 年 6 月 26 日演算法 VS 佛法|宗萨钦哲仁波切谈佛典汉译 (二)
2020 年 12 月 28 日宗萨钦哲仁波切谈佛典汉译 (一)
2020年的秋天,宗萨钦哲仁波切应圆满法藏佛典汉译计划的邀请,为近六十位译者和佛典汉文专家娓娓道来他对佛典汉译的想法。
翻译就是一种修行
■ 不为说法,今天谈“译经”

今天来到这边,并不是来说法的。
讲解佛经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得花费许多天的阅读及准备。基于时间不足,加上我本身又是一个很懒惰的人,根本也不想阅读。有一种说法是,整体而言,若不是登地以上的菩萨,是不会懂得佛经到底在说什么的。对吧?而且我根本没有任何翻译相关的经验,以前我的几位根本上师们在与西方人士交流时,我曾稍微翻译过几句,但也就是几句话而已,而且还根本不是跟佛法相关的语句,只是一些类似“要吃这个”、“要喝那个吗”的话,当时就决定了,以后绝不可能当翻译,因为实在是太累了。
再来,我的藏语一点都不好,尤其是我的发音,完全就是混合的。我出生在不丹,可以算是半个不丹人,而我的师长们来自各地,例如德格、囊谦、卫藏(译注:俗称前藏与后藏)。小时候,老师们就要求我必须要背诵文法书,所以那时曾从头到尾,背过一部名为《正字学.语灯》的论典。直到现在,它一点用途也没有:我的拼音,至今还是一点也不正确。《三十颂》则大概学了三、四天吧,现在也已经忘得一干二净,只约略记得顶礼句“敬礼大自在”等几句而已。当然我有我的理由。不只是我,藏地大部分的大学者,尤其是那些精通经典的堪布们,大部分在藏文方面的造诣,也都不是太好。Wangcukla就知道这种事。
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晓得:那些所谓的格西、堪布,他们认为应该学习经典、中观、因明、般若等学科,但若问他们《三十颂》、《正字学》等,他们就会觉得那些是在浪费时间。我的老师之中,不乏多位娴熟精通经典之人,比方说堪布仁千,就实在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,尤其是中观、因明的造诣极高,但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办法写得很好,他根本也不太在乎这些。这是我们这世代人的样子。
但谈到翻译,则必须精通文字学、语言学(译注:仁波切用藏语说出这两个学科的名字,应系指涉广义的文字学和语言学,而非西方传统意义下的学科),由于我在这方面并无涉略,所以其实没什么特别能拿来跟你们谈的。我的祖父“依怙主敦珠法王”在语言学、文字学方面的造诣是声名远播的,他极为重视藏文的书法。有一种名为Tshugs ma ring体的字体(ཚུགས་མ་རིང,长脚行书),我前后大约学了两年吧。当时用一种木板来当习字版,在上面要涂一些水,抹一点油,再在上面洒一点灰,使用白色粉末在木板上划线,类似墨斗线,光是学怎么样弄好那个线,就要花费一个月才学得会。之后还要自学制作竹笔,这也要花好几天。
也得学制墨:要把我们拿来吃的青稞,去炒得非常黑,炒黑了之后再加水,然后要放置一两周,它才会变为纯黑色。接着,要在木板上要写得如此的长(大约1英尺长)。像这样子,我大概学了两年左右,在被逼迫的情况之下,学了两年,而且教导者还是位藏族上层人士--桑竹颇章,他的书法非常知名。我向他学了两年以后,桑竹颇章去了美国,我的文字学习就此中断了。现在偶尔写一些短短的文字,写长篇就当然没有办法,只写一些短的,过两天后,回头去看两天前写的东西,连我自己都看不懂。
■ “翻译”就是一种修行
那么,今天来到这边,期待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?主要想谈“翻译非常重要”这件事。翻译之所以重要,原因有很多。在座大多数应该都是佛教徒、或者说在修行、实践佛法的人,但也许有些并不是,有些人也许只是在学习、练习翻译。如果您是佛教徒,以非常清净的心、正确的动机来做这件事,那么,“翻译”这件事就算是一种修行了,可以称得上所谓“修行佛法”。
当然,不可能总是想着“为了等虚空一切慈母有情众生,发起大乘心”吧?没那么简单的。但是如果每周能抽出半分钟的时间来想想这点,就算是非常有意义了,而且这应被视作你们的修行。对于其他上师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,我并不清楚,不过,不是有称为“十万大礼拜、十万曼达”的修法方式吗?我认为你们做翻译,其实就可以跟这些方式相提并论了。
这种主张其实也不是我的发明。比方说像现在这部经(《圣最上三昧经》)之类的,其中提到“讽诵、执持”,所谓“执持”,比方说你将经文放在自己的家、包包里面,光是这样的善根便已是无上善根,佛经是这么说的。所以你们能够翻译这样的经典,让他人能够认识、能够了解其意,这样的善根,绝对是所谓的无上善根。今天最主要,是要跟大家谈这些。至于我们之所以要翻译的其他原因在于…我要谈很多原因,但讲的时候会有些前后次序紊乱,我并没有写笔记,因此我不会特别安排着按什么次第来讲。
■ 佛法仍然鲜活,仍有人在实践它

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学习与佛法相关的知识,比方说在喜马拉雅山一带,有很多的孩子,是从五、六岁就开始学习佛法知识,直到成年的。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,因为从一般来说,当然有很多佛法义理极为渊博之人,但也有另外一类人,是本来完全不是佛教徒,但是后来关注佛法,后者也许用五、六年时间去学习,这是一类。但后者与从小学习佛法的人,还是有差别的。目前为止,从小学佛的人还是很多,未来如何当然还不可知,(毕竟)在寺院当中,年纪小的僧人,是越来越少了。
不仅如此,到现在仍然很还有为数不少的人,他们不仅是学习内道佛法,他们还会去实践佛法,甚至试着做闭关,依止上师,这些人都还存在,这点十分重要。当然,同样的,将来会如何,我并不清楚。比方说在南美洲的马雅文化,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主题,相关知识相当丰富。可是根本没有人能具体说出“马雅人他们到底具体做了哪些事?”。对于马雅人戴了什么样的帽子、他们吃什么样的东西、他们怎么样做事情的,根本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所以然来,就算有人说了这样子的话,都可能已经入狱了。
例如,据说在过去马雅文化里,人们很喜欢决斗,他们的说法究竟为何,当然是我们所不知道的,但据他们的说法,死者将能够上天堂,于是,亡者才是胜利者,结果很多人大概都为此而死。这就是想法的差异:如果是我们要跟别人决斗的话,当然是盘算着如何能够毁了对方,但他们决斗时,却是在想:“我怎么样才会死呢?”所以连思想都不一样。有很多人在研究他们的生活习惯、生活方式,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过日子的,也有很多这领域的专家,可是他们并不会真正的把这些观念,放在自己的心里、并去实践它。
注意一下,我们今天并不是只是在谈藏传佛教,在我的看法中,斯里兰卡跟缅甸等地方,都仍然有相当优秀的师长,但是他们也在凋零当中。在诸位汉传佛教的环境当中,仍然也有很多优秀的僧人及诸如此类的人,这太重要了。这些现象仍然存在,在还有人在学习佛法义理的时代,我们要能够更加努力,这是非常重要的事,其实讲起来,这是极其稀有的,看到Wangcukla这样的人,都是非常稀有的事,像他穿着这样的僧袍:这一个已经延续了2500年的时尚,而现在居然还有人穿着这样的衣服,怀有这样的思想。
现在已经看不到iPhone二代、三代,博物馆里也许还有,但我们现在生活中根本就看不到。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懂得思考的话,这一类的现象就很重要。如果今天大家都完全不在乎,也根本就不追求佛法了,那当然另当别论,但并不是这个样子的,还是有人在乎、有人追求,真诚追求着解脱与一切智的人,也仍存在,仍然有人的目标是“饶益一切有情众生”。所以还是多多少少有些人,秉持着如此良善的动机,正在朝这方面追求着,但是也有很多人的目标取向是另外一回事,有些是为了商业,也有些人是为了名声,还不只如此,比方说像正念,在西方某些人,他们可能还蛮有兴趣去关注像是寂止、正念这方面的佛法。
■ 影响力的消长:佛教徒若不把握诠释的话语权,商人会开发出另一套东西
举例而言,英国公民生病的时候,国家会出很多钱,因此政府的负担当然很大。但诚如诸位所知的,在当代,我们心里的问题很多,尤其像西方人他们,有很多人的内心非常的痛苦。为了要解决心理方面的疾病,当然还是会有人服用药物之类,但在后来有段时间,约莫十几二十年前吧,他们发现,佛教里面所讲的奢摩他(寂止)这些修行或者修练方式,会对心理有帮助,因此,他们从中看到了利润。利润何在呢?因为你只要待在那边,根本就不用去制药,当然也不用上医院,只要病人来了,就告诉他:“你就坐着。”这就是为什么“正念”的市场如此的大。
我自己也有一个正念的APP喔!在这个APP里面,有着关于“寂止”跟“念住”这些方式的商机,他的商机是用百万、十亿美金在算的。可是这跟“进入佛法”,完全是两码子事喔!所以我们应该要考量到一件事实就是,假使作为佛教徒的我们总是一成不变,但那些有商业头脑的人,头脑正转得飞快,过了二、三十年以后,我们的影响力,可能比他们更小。这大概可说是真实状况。例如是瑜伽的发源地在印度,可是现在要当瑜伽老师、想拿到一张瑜伽的证照,若你想要证照非常有公信力的话,你得要到美国去。在这样的状况还没发生之前,我们必须要多做一点什么。
我主张要翻译大藏经这一类的经典的时候,有很多人反对,他们说:“他利用了佛法,去做了什么什么事。”但就像前面所讲的,我之所以呼吁要做这件事情,是因为我们如果不做的话,“那些人”会做的。那些人(商人们)会从中得到商业利益,当然这不是说不能牟利,如果说他们是翻得很好、很正确、很有意义的话,当然可以翻,但是他们肯定不会朝这个方向去翻。
像当我们谈到“寂止”时,我们不会只说,“保持心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就叫做寂止”,不会是只是这样,因为我们的目的,是要证得解脱及一切相智,既然要证得解脱跟一切相智,因此必需要先净除烦恼。而如果要净除烦恼,就必须要有胜观(毗婆舍那)的智慧。若要有良好的胜观,就必须要具备寂止。而为了要成办寂止,如同经典里面所说的:“止由离贪成。”就算不能完全舍离世间,但至少要知道世间有缺陷的…..等等。
然而,现在开办所谓“正念课程”的这些人,他们完全不会去谈“要离于世间贪欲”等的话题,为什么呢?他们的正念课程完全着重于此世,强化“如何让世间、此世变得更好”的观念,他们如果谈“舍离世间贪欲”,就根本没有商机了。这就是推广翻译的原因之一。
■ 转译之难:语文乘载的涵义,与其所处语境、社会文化息息相关

至于第二个原因,就是像我这种没有什么学问之辈,所谓的名相、名言这些东西,太重要了。我还是懂得这层道理的。这些都非常重要,但也已经越来越衰微了。
以不丹来说,假设有对男女在谈恋爱,我讲的是40年前喔,40年前的不丹男女,他们不可能说:I love you,绝对不会这么说。你们汉人会这样说吗?会说?你们自己去想想看,反正这两人是不会这么说的,藏族也不会这么说。如今,不管是藏人也好,不丹人也好,喜马拉雅山一带的人也好,若要表达爱意,一定会用英文讲:I love you。
在不丹,若一对男女谈恋爱的话,他们会用的当地词汇sems shor(སེམས་ཤོར)来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意,意思是“完全为对方失去自己的心”。(倾心)sems shor是个非常有力量的词,代表心里面原本有的东西,被人家给带走了,应该不是说被夺走了,应该说是不自主地丢失掉了、我最重要的那一颗心,被那个男的给带走了、被那个女的给带走了、不由自主的给带走了…在其中,你可以看到文字的力量。
然后在藏文中,可能就是说sems pa chags(སེམས་པ་ཆགས,心生贪着)。sem pa chags当然也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词,chags(ཆགས,贪着)它有很多的解释,其中一种就有点像是:卡在那边,完全动弹不得,非常顽固的,想丢也丢不掉,只是卡在那个状态之中,那个就叫做“着”。所以“贪着”的意思,就是“附着在上面”,它的意思很强。所以当“心附着在上面”或者“失去我的心”这个词,被翻成love的时候,我总忍不住想:“啊…不是这样吧?
汉字怎么解释love这个字?爱?爱这个汉字是什么意思?
(Bella:我想传统的意义,比较接近“拥有的欲望”,特别是在佛经教义之中。至于在说基督“爱”的定义,会说是“大爱”、较为正面的解释。当然,这个词现在已经比较中性了,大多是正面的意思。)
■ 观想西方:西方观念深植东方人的心中
我要跟大家谈这一点,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起了太大的变化,而最大的变化发生在西方国家。藏族有很多人会说:“宗萨钦哲?啊!他在观念上是西方人。”可是英美人士对我对常有的批评则是:“他反西方,与西方为敌。”这些都无所谓。无论如何,西方的影响力是很大。前几天趁与一些堪布、上师们讨论时,我稍微提了一下,但是没有讲得很完整。如果我们考量整个世界的历史,西方的强权力量是非常大。像是印度被他们统治的历史,就已经有上千年(译注:仁波切应该是从亚历山大时期开始算的)。
先前跟两位教授(韩老师、侯老师)开了一个玩笑,我当时就讲了,你们所谓的汉人,不管是中国的汉人,新加坡的汉人或是台湾的汉人,我可以说:“你们几乎没有文化可言,但我们不丹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,我们还可以宣称我们有文化”。你们还是有留下语文,饮食习惯也留下来了。但是你们已经把西方人观在头顶上、观在心间,所作所为都在模仿西方。只要还可以负担得起学费的话,不管你的孩子是男孩或女孩,你都会把他送到西方去接受教育,这大概是势不可挡的,因为人们的想法已经西化了。
但是在座诸位,身为译者,你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情况。在运用名词的知识(或文字学)方面,我们受到太多西方观念的影响。然而,无论是名相或语文本身,它早就起了很多的变化,请诸位译者留心这点。同时,也请不要误解,当我说“语文会产生变化”时,并不是主张你应该回归两千年前的思想,只是认为你们需要察觉到这个变化(语文会变化)。
从全人类文化的角度去想时,我对现状感到非常忧心。讲到佛法的时候,它(语文变化)的层次则又更进一步。比方说梵文duḥkhaḥ这个词(苦)古代藏族译者,我们称他们为译师的这些厉害的人们,他们应该是绞尽脑汁,才再把duḥkhaḥ翻成藏文sdug bsngal(སྡུག་བསྔལ)这个词,他们应该想得非常的久。当然我们藏人的习惯是说,这些人都是亲见本尊后,所以能如何如何。但是我想他们如果从人类的角度来讲,应该是殚精竭虑的。
duḥkhaḥ这个词,或者是藏文当中sdug bsngal这个词,它本身甚至富含着我们一般意义下的“乐”这个意涵在里面。可是像在翻成英文的时候,他们翻成suffering了,也就是“受苦”,这样转换,大概就没有把duḥkhaḥ的意思转过去。你们汉文中怎么翻译duḥkhaḥ的?(翻译:苦。只有一个字。)
印度作为一个数千年文化的文明体,它肯定蕴藏著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文化。先前我跟一位很厉害的日籍翻译谈话,他提到日文当中的[53:47]mu(无)可以对应到“空性”或“空”这个词。你们汉文怎么翻stong nyid的?(翻译:空,空性。)所以语言换在不同的地方,大概有不同的认知。
■ 词汇:熟悉会促进理解

最近在读一本书,汉人写的,它非常厚,没有办法马上读完。当然以下是我个人意见,他主要是在讲唐朝僧人玄奘的事情,那故事里面既有猴子,也有猪,什么都有。不过里面有件非常稀有的事:那只猴子居然叫“知解空性”(悟空)!我觉得这实在是非常庄严的事,我在想作者到底是何等匠心独具,居然会这样子做。为什么呢?一边名叫“知解空性”,同时一边闯大祸、最糟糕的,也是他呀!他胡作非为又很有能力,同时却也依教奉行。我想当时这作者是肯定绞尽脑汁了,他居然写出“解悟空性”这样深邃的意涵,又有故事性,还可以讲给孩子们听,所以作者肯定是费尽心思的。
我之所以要与你们分享这段话的用意在于:在翻译的时候,你们真应该想想这一方面的事情。固然,现在你跟一个孩子说有一只猴子,他的名字叫悟空,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他反正知道悟空是他的名字。可是因为一直听、一直听,他的耳朵不断的听到“悟空”这个词,总有一天,他也许会问你:“『悟空』到底是什么意思?”然后你就会有机会开始跟他谈空性了--谈五蕴空、诸法皆空,甚至谈整套的般若波罗蜜多都可以。
又如梵语中[57:17] karuṇā(悲) 这个词,它的意义非常的广,英文只能用compassion来翻译它,根本不充分!用compassion这个词用来翻“悲”,只能说勉强凑合著用,用于“缘有情生悲”的时候还勉强可以通,但如果要翻译“缘法悲”与“无缘悲”,这个词就显得相当牵强、费解。我后面还会补充这点。现在有许多的汉族翻译,他们是用既有的英文译本,然后再把它翻成汉文,对吧?英文compassion这个字,它就是在英语语境下的东西,所以这些状况,都是我们值得深思的。
同样地,“无我”这个概念也是一样。在我们要讲这个话题之前,再补充一下,我们在座的人,大概都已被灌输太多西方概念了,西方观念已经深植于东方人心中。而西方观念中,包含很多基督宗教的成份,就算你不喜欢基督宗教,也会受其影响。我有很多欧美的学生,他们并不是基督宗教的信仰者,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否定基督宗教,认为那宗教是无稽之谈的人。可是他们所使用的词汇、他们的文化、他们的生活方式,仍充满太多基督宗教的色彩,所以那种色彩,有点像是污垢,或像是臭味,你很难将它完全清除。
然而更加严重的是,这些汉人也好、印度人也好,或是藏人当中,凡是带有西方概念的人,他们根本就将西方文化是奉为圭臬了。例如基督宗教信仰、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当中,它们都有个“大我”的观念,也就是soul(灵魂)的观念。soul该如何翻译成藏语?(藏人听众:srog[སྲོག,魂], tshe[ཚེ,寿])看吧?现在该怎么翻这个词咧?没这个词呀!我们根本没这个词。因为在我们的语文没有soul的观念,所以在谈到“无我”的时候,就不会有争论。
补充一下,像诸位是身为汉地的译者,在汉文化当中,有所谓的“道”,它真是非常博大精深、智慧卓尔的。当然,我不太熟悉这些,只是稍有涉略,但是应该是它的词句、意义都应该是相当丰富的,对于这点,你们应该要关注。
■ 抉择词汇要多方考量
你们汉族过去的生活,“佛”“道”的关系其实应该很密切。我先前读过一本书,称为《红楼梦》,读了三十页以后,我就把它扔了--它的资讯量过多了,那位王先生实在是被提到太多次,我根本不知道那位王先生是何方神圣。(Jennifer:王熙凤,她是位女士。)喔?王女士。这本书有精简版吗?有没有精读本?
再回来谈“无我”这个概念,只要这个文化中有灵魂的观念,你要跟这些人谈“无我”,基本上就不知从何谈起,就算讲了,他们也是怎么想都想不通。“无我”固然如此,对他们来说,“前后世”也很难接受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的文化当中有灵魂观,而灵魂是一种“不变的法”。
所以,灵魂有时候钻进猴子身体里面,猴子的躯壳崩坏,再换到猪的躯壳,猪的躯壳坏灭后,再换到一个人的躯壳…他们钟情于这样的思惟模式。因此,对他们来说,所谓的“无我”,应该:是“要先有个『我』”,然后“我”不见了。所以以他们的理解而言,所谓“前后世”,应该是指非常实在的、真的存在的某个有情,会从这边钻到那边,再从那边钻到另一边。
当然,在我们佛法里,关于这些方面都是挺难解的,也有很多东西得学。在佛经当中--例如《般若经》--有所谓的四重般若, 也就是“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色不异空,空不异色。”佛陀也给了我们这四重的复杂性,一层又一层的复杂,搞成了四重,诸如此类。所以在传达语义、运用名相方面,真的要广泛学习、思辨。就像刚刚所说的,翻译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尤其是当今佛教的重要性越来越强,个中理由很多。在众多理由当中择一而言:全球的科学与经济都相当发达,与此同时,有什么副作用呢?副作用就是我们的工作都会跟着科技跑。
Ngawang!algorithm的藏文怎么说?可能有这个词汇的。
(Ives:演算法。)
(Wangcukla, Ngawang:rtsis thabs.)
rtsis thabs?Ok. 这个词在中文怎么说?
(翻译:演算法。演算就是rtsis pa,法就是thabs)
这样呀?我猜可能这个藏文的名词是从中文翻过去的。看吧!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,讲到名词、名相就会遇到这种状况。
继续阅读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