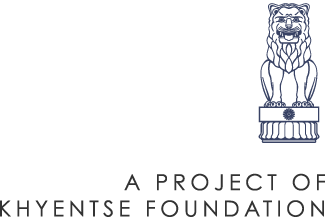翻译就是一种修行|宗萨钦哲仁波切谈佛典汉译 (一)
2020 年 12 月 28 日宽宏的眼光与诗意的情怀|宗萨钦哲仁波切谈佛典汉译 (三)
2020 年 12 月 28 日宗萨钦哲仁波切谈佛典汉译 (二)
2020年的秋天,宗萨钦哲仁波切应圆满法藏佛典汉译计划的邀请,为近六十位译者和佛典汉文专家娓娓道来他对佛典汉译的想法。
演算法 VS 佛法
回到上一段的演算法。
■当“演算法”主导未来,佛教的“叙事”便显得关键

为什么要谈演算法呢?因为要谈佛教的重要。佛教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很多,其中一点便会涉及演算法,也就是藏文翻为rtsis thabs(རྩིས་ཐབས,演算法)的这个字。待会儿我们还会再补充这点。在我看来,当初把它翻成rtsis thabs的时候,应该是从中文翻过来的。这些学文字学、语言学的人,他们对于这种[借词、外来语],会有很多用词的考量。
例如现在的这个冠状病毒,藏文翻成tog dbyibs(ཏོག་དབྱིབས,冠状),决定译词这种事就得仰赖语言学。以我来说,我可能会就不去管那个Corona原本到底什么意思,就直接采用tog dbyibs这个词。Corona的意思本义好像是日光的毫端吧?对吧?Corona是什么?(听众:冠。)“冠”吗?当初是否按照字面如实的去翻,到底翻得好还是坏,其实也搞不清楚。在我的观念里面,称之为“Corona病”,也就可以了。
就像刚才提到的演算法,在藏语中被翻成了rtsis thabs。也许这样翻译是可以的吧?也许是可以的。无论如何,在未来,演算法也许会是整个世界的主导者,跟我们的未来是密切相关的。
回到我的主题--“佛教非常关键”。为什么佛法会扮演关键角色呢?因为对于六道众生、特别是人道有情来说,“故事”(叙事、说法)很重要。只要有故事,接着就有“人生目标”这个主题。对了,我现在是用科学方法在谈的喔。以确尊法师、Wangchukla和我三人为例,如果你问他们二位为什么要穿成这样(按:穿着僧袍),因为他们有个目标,他们想成佛。“为了成佛”本身就是一套说法--他们二人相信这一套说法,因为他们相信这一套说词,所以他们为了成佛,而剃头、剃胡子。
人道、有情,都需要有一套说词,有了说词,于是出现了“前程、目标”。在美国,当前人们最乐于贩售的说词,就是“民主”。我们也心醉神迷、呆愣出神地望着这个说词--民主。因为相信民主,所以你的人生目标、前程就跟它扣连在一起,其中有些人是老师,有些是医生,与这个大的命题相关的责任,还有他的教育,都扣连在一起。但据说二、三十年后,这一切将不复存在。比方说,可能不再需要某些医生了,因为演算法可以取代他们,演算法比医生更厉害。医生时不时也会沮丧,不免会感冒,但是演算法不会。刚刚我们不都去了洗手间吗?医生偶尔也是要上厕所的。
同样的,二三十年后,堪布他们也要失业。例如你今天想要了解《入中论》里关于远行地的“彼至远行慧亦胜”这一句的意思,(敲了一下桌子)你只要按一个钮就可以了(根本不必问人)。如果这种状况越来越普遍,那我们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?要干嘛呢?到底要医生这些人干嘛呢?届时所谓的民主啊、社会主义啊、生而自由这些概念,都会变得似乎无关紧要了。
现在还存在着一丝丝值得相信“民主”这套说词的理由。例如,假使我是一个医生的话,我会提出要求,表示我要有什么样的权利,但过了二三十年,就没这回事了。假设到时候这些事情都不复存在,届时所谓“自我”到底是什么呢?它的意义何在?它的目的为何呢?形势越是如此发展,佛法会越重要,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翻译的原因。[翻译过程中,]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问题、很大的问题。例如,整体来说,翻译本身就很困难。其次,翻译那些2500年前的话语也很难,除了我们这些人以外,谁都没兴趣。因为没有利益,看不到什么好处--我指的是这些金钱利益。而且这工作很无聊,工时又长。
■ 转译之难又一例:理解词汇的内涵
某方面来说,教法也正在式微,现在这部《圣最上三昧经》就是这么说的:“我入涅盘后,一切比丘虽皆读诵,我所宣说十二部经,然于上者,教令为中者,教中者为下者,教下者为上者,教中者为下者、末者;亦即:非真义者,谓为真义;于真义者,谓非真义。如诸外道,各各谓我经典,非谛非实之所言也。”佛的意思是,将来人们会按照自己的意思,把佛法给弄乱。因此,你们有得瞧喔!一件有利益的事情,往往困难重重。
一般来说,内道佛法弘扬到各地的时候,各地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语言,语言使用习惯跟理解。以此经而言,里面有个词:bon chos(བོན་ཆོས,方术。直译则可译为“苯波信仰”)。你怎么翻译这个词?
(译者:不见得有信实的证据,仅凭借着自己的信仰传统而行动。)
嗯。如果bon chos专指苯波信仰,则可说是我们藏地独有的名词。同样的道理,在不同的地方,人们的习惯风俗也不同。像是经文中的spyug pa(སྤྱུག་པ,驱摈)这个词,大概就是英文的exile,汉文当中应该有吧?汉文怎么说的?古文中有这个词吧?
(翻译:有的,有的。)
再来,mig mangs(མིག་མངས,棋奕)汉文怎么说?
(翻译:类似chess。)
嗯。还有rta rgyug(རྟ་རྒྱུག,赛马),现在当然还有赛马了。诸如此类,经中提到了未来世上的人们处世的方法、思维的方式,乃至于娱乐的方式,应该还有很多其他事。在[佛陀]当时,对于集会、聚众这件事情有过评议,也许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喜欢集会。
■ 佛法在西方的传播尚无标准,但在汉藏两地则早已形成既定的传统
我既没有办法解释这整部经,我也没有打算这么做,但我们可以一起阅读几段。在这部经的一开始有提到梵语,这是值得思考的。整体而言,当佛法从印度传到汉地、传到藏地,传到日本的时候,它弘扬的方式就各有千秋。同样就像是现在,它传到了美国、欧洲、澳洲等地,各地的发展方向也互有不同。如今在西方,佛法的研习者,主要是修习语言学的少数学者。
在1950-60年代(约六七零年代),抽大麻的嬉皮们之中有些人注意到了佛教,也有人注意到印度教,出现一些关注东方宗教与文化的人。当时此类的人还不少,但他们就只是像这样的:“看这个!喔!厉害。”然后就没了。(探索猎奇,浅尝辄止)没有人想要从头到尾了解这一切。他们也去沾一下印度教,学一点瑜伽。西方人就是由这一类人开始注意到佛教的。据说最早去澳洲传佛法的,是一个汉人,听说在两百年前,汉人首度到了澳洲,当时把观音像也带去了。这件事被视为佛法在澳洲的开端。
至于美国,佛法的弘扬则与越战有关,越战结束后,一些越南人来到了美国,所以带去了部分的大乘佛法,所以有些零星的弘传。二战以后,有些美国人开始注意到“禅”,但是他们的“禅”好像都还在处于跟花道、茶道混为一谈的阶段。对他们来说,弘法并没有特别的规范,去要求他们“这件事情要做,那件事情不该做。”
但是藏地的情况就是另外一番风景了。法王赤松德赞、赤热巴坚他们的权势极大,藏语称之为btsan po(赞普,藏王。赞普一词,做形容词时,义为严峻)。他们的话语很有份量、有强制力,因此他们对翻译做了很多干涉。他们将数以百计的孩子派到印度去,只要稍微聪明的、有思考力的,就会被派去。这些孩子被告知:“你得去印度。”才不会先征询孩子的意见,例如:“你要不要去印度呢?”只有一句:“去!”
赞普会支应这些人的费用,不仅如此,供养师长的礼金也都计算好了,例如:“这是你个人的费用,至于黄金可不是给你的费用喔!这是供养上师用的。”所以会编列预算,诸如此类的规范还有很多。我想,此举对翻译事业帮助应该是很大的。今日肯定没这种事了。现代的人都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以我来说,我想过:“假使可以成为一个佛法的金正日,那该多好?”我发愿变成一个佛教的金正日。如果此愿实现了,我就会禁止使用compassion这个字。
■ 问答

问:仁波切提到“要深入东方文化,学习佛法名相的重要性”,请问如何更好的深入东方文化?
仁波切:你愿意这样想,本身就已经很好了,大部分人连想都不去想。有些人会为自身 的文化感到难为情,很多人是这样子的,所以能够这样问就不错了。与这方面相关的疑惑,多多益善!至于其他人要怎么做,都无所谓,随他们去。不过,就今生来说,无论文字、语言等一切如何变化,佛法仍然是重要的。这点得保持下去。
问:许多的佛学名相由于和今日时隔过久,已与现代语言已有脱节,所以译者要大量学习这些不符当代语境的佛学名相吗?翻译时要运用这些名相,还是直接用当代语境的名相?
仁波切:这是很关键的问题。我对古代语文也不是很懂,可是现在仍有许多学者们懂得古代语文,所以或许编出一本古代语文的字典,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我坦白说,我认为比起古代语汇,现代语汇更加难懂。《孙子兵法》翻成藏文版之后,我读了一下--啊呀!一句都不懂!看了英文版之后,就比较看得懂了。还有《道德经》,它似乎有很多不同的英文译本,其中有一些,我读了以后,产生了“哇!《道德经》似乎很重要呀”的感受。还有汉地的六祖慧能,他所宣说的《六祖坛经》实在太重要了,真的。《六祖坛经》的英文译版,好像也是各式各样。
我们前头半开玩笑、半认真地讨论西方,但是也必须澄清一下:有许多西方人相当的优秀,有些人思想卓越,有的真的是表里如一,有些对佛法与上师有极强的信任感与信心,这类的人相当多。然而,我还是会觉得,假使全盘移植他们的文化,将会变得很困扰。例如珍·奥斯丁写的《傲慢与偏见》有翻成汉文吧?
(翻译:有的,译本很多种。)
我不太敢相信他们的翻译品质。《理性与感性》有翻译吗?
(听众:有的。)
为什么说我不相信他们的译本呢?因为里面有很多专属于英美人士的情感,但我觉得你们汉人很难体会这些吧?
例如《傲慢与偏见》的那个妈妈生了三四个女儿,为了要给她们找伴侣,妈妈攒了一大堆财富,汉人的妈妈应该也会这么做。然而,文中有些情节是专属于英式文化的成分,例如社交舞──男女共舞,我可不知道汉人是否会担心在出席舞会前担心“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参加舞会呢?”。到了当代,当代的汉人已经被完整灌输了这一切思想。现代的汉人已不再有《红楼梦》的情感,跟现在的汉人说“悟空”,对他来讲,就只是一只名叫悟空的猴子,别无其他。但像是那群猴子住的“花果山水濂洞”是个有瀑布的地方,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反映出独特的汉人思想模式了(却无人问津)。
■ 思考方式有别于我们,并不代表错误;不要自我矮化、画地自限
我再继续谈一下这本经(圣最上三昧经)。经题用梵语及藏译两种文字记载,这件事非常重要。如此一来,在回溯经典时,马上可以追溯其来源为印度,就点十分重要,对吧?那个时代人们的学习方式与思想便是如此。
还有件事要跟你们谈。普遍意义上而言,每个文化都有许多自己的优点。例如,西方人擅用index(此处解释为索引、记录),我认为他们在这一方面可谓非常杰出。但藏人就没什么这类的习惯。当然也许也会有例外,但我认为在汉人以前的文化里,应该也有记录的习惯。但在印度,则很少有“记录”。为什么呢?在印度思想当中,所谓的“学问”是不可以留在书本里的,必须记到心里。
比方说在梨具吠陀的教育当中,他们很重视“口耳相传”,也就是:一个上师讲、一个弟子听的“口/耳”传承。就像我们的佛教名词里也有个“声闻”,意思就是听到、闻得。在这样的思想底蕴下,历史、年表的观念也就不存在了。人们一谈到印度的时候往往是诗歌、花朵、饮茶等话题。后来,当今的印度人他们也受到了英美思想的洗脑,所谓的“现代的印度人们”,他们怎么看待过去呢?他们认为:“啊!那是落后的、迂腐的。”我认为他们这样的看法是一种错误,当然也有一些人抱持不同的观点。从事翻译者的人应该会懂这些的。
例如,佛说般若时,地点是灵鹫山,据说他在山顶上,与上万名阿罗汉共处。假使用现在的科学头脑来看,哪有可能容纳一万人?就是10、15个人大概也难以容纳得下。你们也晓得的,从某个角度来讲,有所谓“这些都是佛化身”的说法,这样说也可以吧?我的想法是,当时的思考观点跟我们不一样,也可能跟当时的语言使用习惯有关。我们现在也有[这种与事实不符的]这种说法,像是:“我永远爱你!”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是妄语。但它就是妄语,而且是最大的妄语。但这种情形依然存在的。这种叙事的目的,是为了要衍生些什么。因此,看待这一类叙事的时候,心胸要稍微宽一点。这是一点。
■ 人们读经时常忽略的细节:序分

再来,“如是我闻,一时”这段。其实在我看来,这别有深意。一般来说,“如是我闻,一时”这句话很简单吧?也就是:“在某个地方,有一次,我这样听到了…。”但若不是我们佛教徒,对于其他印度人来说,当他们听到梵文里的evaṃ mayā-śrutam(如是我闻,一时)时,对他们来讲,其中有很多的可谈的。
这所谓“有很多可谈的”并不是对佛教徒来说的喔!而是对一般人来说的。这种叙事方式能够引出后面的内容。举例而言,当经中说:“在那一次,我听到了。”这表示“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场合”呀!还有,经中只说:“我听到了。”并没说有说:“他说了什么什么。”这实在非常重要。为何呢?这就是谦逊。这表示:“我是这么听到的。”用如今我们的话来说,人们会说:“他就是这样说的!”此外,这句话(如是我闻)也表示:“当我听到那席话的时候,还有别人在场呢!”
内文还有“与三万比丘…”之类的──表示什么都不懂的呆瓜,可是不在场的喔!会上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。这段叙事本身是非常庄严的,在那里面有天人、龙…等。这些叙事都是非常具有力量的句子。就像现在的G7、G8高峰会议,与会者要嘛是日本首相,要么就是俄罗斯总理、美国总统,报导可不会说:“有一匹马、一头驴出席会议。”这点非常重要,为何呢?因为听众本身就不同,有:天人、龙族、罗刹、饿鬼等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听进去多少,但他们在场。
佛有时候会说:“轮回的本性为苦,苦的成因是烦恼。”此时,听众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内容。假设这里面有位持明者的话,他听到的可能是:“轮回的本质是乐空。”对他来说,烦恼的自性就是智慧。因此,听众的理解是殊异的。这些[关于听众身分的]叙事是如此地重要。这部经(圣最上三昧经)还是一部短的经喔!若像是《华严经》这种大部头经典,一开始就在描述出席者:天人某某某、天人某某某…。讲完天人以后,接着描述:龙王某某某、龙王某某某…。光这个就可以写三、四百页了。这些叙事不只是反映出听众的身份,还说呈现出当时人们的思想。
这些资讯实在太重要了。我觉得,当你们在翻译的时候,应当尽可能地将它的味道、风味、滋味、感受给传递出来。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一部经,它最主要的因缘是甚么呢?要知道,每一部经它都有各自的因缘。例如《无垢称经》(维摩诘经),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一部经,重点都在“到底要不要去说一句:『How are you(你好吗)?』”就为了这个,于是该经就出现了。同样地,每一部经都是这样。它们各有出现的因缘背景。
■ 本经最令人惊叹的地方:文殊赞扬佛陀“什么都没说”
这部经之所以会出现,就是因为“当时佛什么都没说”。这令大众起疑,开始窃窃私语:“他怎么回事?”“他到底要说什么?”“搞什么?他为什么会不说话?”“他什么都不做也不说,怎么回事呀?”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喔!我是这么想的。我觉得佛当时就只是待在那边,然后下面的人就开始窃窃私语:“今天要说什么呢?怎么什么都没说?”当然,在场有很多人。听众可能拐旁人一下,问:“现在是怎样?”你推我,我推你,大家都推别人去问:“你去问一下!你去问一下!”推到最后,就推到至尊文殊师利身上。他们对文殊说:“你去!你去嘛!”这是我的剧本,简言之就是如此。
于是文殊就起身了,并且讲了一些奇怪的话。他是一个奇怪的人,说的话也很奇怪。他并没有直接问:“呀!你今天什么都没说,是怎么回事?”他反而赞叹说:“哇!你真的太厉害了!你今天居然什么都没说。太厉害了!”真是夸张呀。他这么说:“甚善日月光,默然而不照;甚善珍宝藏,不施贫乏众;甚善人中王,请从三昧出。”等,意思是:“实在太稀有了!你居然什么都没说。”我个人对于这整部经觉到最惊叹的地方就在这段,尤其是“甚善龙王者”这句,我对于这句话很有感觉,这很稀有的,他说佛是龙王。
整体而言,做为佛教徒,心胸要宽一点,做翻译的人可能也要心胸宽一点。举例而言,假使有个佛教徒问你:“佛是谁?”而你回答:“佛是龙王。”那你可能会被揍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龙有时被视为傍生。在印度,假使不特别加以区分的话,人们会认为龙、天人、寻香(干闼婆)都是一样的。就像刚才说的,召开G7高峰会时,出席者都是日本首相、美国总统、澳洲总理这类人。可能是同样的道理吧?佛在世时的听众,都是:天、人、风天、水天、难陀龙王、优波难陀龙王、五髻干闼婆王…那些人。对我们来说,这些听起来都像是神话,但应该不能算是神话。
继续阅读: